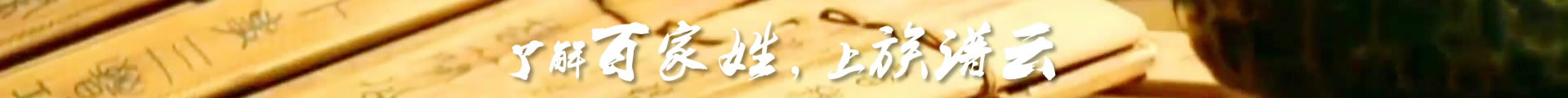论明朝首辅大臣申时行的执政行为性格特征分析
作者:申国祥
时行的行为性格特征有历史研究学者对其作了一些研究,比较典型的学者是陕西师范大学刘莹莹、白燕斌所著的《试析万历朝首辅申时的性格因素及成因》一文,发表《西安社会科学》杂志上,(第27卷第5期,第125至126页,2009年12月。)这是中国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申时行的第一篇著作,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这是一篇从个人角度去探讨心理性格的著作,是一篇真正难得的历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学题材史记。在此文的感召下,我重启了研究申时行的心理、行为规迹的心思,故特作时行的行为性格特征分析,旨在更好地为研究申时行个性特质上提供某些理论上的参考。
一、“维姓”是性格的体现
我们在研究申时行前,对申时行个人并不了解,因为我们不是学习历史学毕业的,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人员,也不是什么爱好者;为什么又研究他了呢,有三个原因,一是我受一位申姓家族得高望重长者的申志均老先生的委托,他要求我要将太平申时行搬上屏幕,故我在开始去了解申时行的为人,便开始学习和参与到这项工作;二是陕西师范大学刘莹莹、白燕斌所著的《试析万历朝首辅申时的性格因素及成因》一文,激发了我这个学习心理学专业的热情,来研究分析他;三是我本人也是姓申,应当为申家祖宗们做点有益的事情。话说远了些,回到主题,我阅读了一些关于申时行的著作,大多数都说他始姓不是姓申,而是姓徐,叫徐时行,其原因是因为“申时行祖父从小过将他过继于徐姓舅家,故时行幼时姓徐,中状元后归宗姓申。长洲文化兴盛,名士辈出;商业繁荣,商贾云集。”(百度搜索“申时行”词条。)这段话说明,申时行在未中状元28岁前,依然是姓徐,且的确是徐改回申姓的,笔者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查阅了关于许多清朝史记的资料,基本上是这样描述的。所以,改回本姓名是真实的,这才叫做真正的“认祖归宗”,徐时行的行为究竟为什么要认祖归宗呢?我们分析认为有如下原因:一是爷爷生前的有心愿,古代明清时期,家训、祖训、上辈的遗言,作为子孙都是必须要遵守的;二是申时行本身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无论是父母亲、爷爷奶奶、老师们的话都十分遵守,从他的婚姻、生子的年龄就可以看出来,18岁结婚,19岁生长子,遵循了什么年龄干什么事传统观念,又能很有主见地为了自己的前程,而苦读书经,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状元梦想。三是他本身是一个学术型文人人才,当年中状元已经是28岁周岁了,张居正则在16岁中举的,可以说,入朝前两人虽然都是一甲状元,但在年龄相差比较大,申时行是社会阅历要比张居正多了十二年,看到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各种社会现象端倪,可以用见多识广来形容;且对“四书五经”有很深的研究,他的代表著作:《书经讲义会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讲,申时行改回本姓,在当时心理上背上了一个大大包袱,那就是改姓报上给朝廷,朝廷会不会批准的问题,给不给改姓的问题,假如不能改姓又怎么办?当然,给改姓当然是好事,这就不用多说了,改姓当时他心理是没有底的,但又是最希望要做的事情,也是有碰碰运气的想法应当是有的,后来他运气真是不错,朝廷同意更改回原姓,将徐时行,改为申时行,当时真有万事顺畅的心理感觉和愉悦,也表现了改回本姓的个性特质,坚忍与意志力。因为他是个十分有孝心人,实现了爷爷的心愿,父母亲的心愿,达到了尽忠尽孝的目的,完成长辈们的心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初步理想与包袱。
二、“维圆”是高智商展示
“维圆”在这里我指的他处理皇帝和宫殿官员之间有有不同意见一种方式,他不想让皇上与大臣们发生冲突和太大的矛盾,或者说尖锐的矛盾,表现出皇上的话是皇上的道理,官员的话有官员的道理,二种说法,从而减少双方冲突或者磨擦。这种生存之道有维圆的成分在理面,但如果双双方为朝廷命官,与皇上身边的人很亲近,最终会导致问题的暴露,结果可想而知,被同僚弹刻,维圆这种短暂的处事方式,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之举,这种办法可以缓解上下级的短暂矛盾,也的确是一种圆滑与聪慧的表现,使皇帝不生气,使官员不受罚,或者少受罚,少冲突,如某某上疏建议言辞过激,诺露了皇上,结果皇上很生气,准备杀了他…,当时,在申时行圆滑下,免去了死罪,放他回家养老去了,朝廷也未发布任何公文对他的处罚。还有张居正在晚年被判死刑后,其母亲狐苦宁丁,在申时行多次圆滑下保留了部分田地房屋才得益生存和养老送终,申时行生前没有多少人给他正面评价,相反在病死前一天,皇上给他封了一个新新名字,官职,但在死后或叫盖官定论。据百度词条评价申时行“在后世多数批评者的眼中,申时行是一个“首鼠两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既无主见,也无能力,更无作为的人,特别是申时行入主文渊阁的这九年时间里的作为,和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实在是过于平静,以至于有点波澜不惊。但是正是有这样的一种类似润滑剂作用的人物的出现,才使大明帝国的经济和民生得以短暂的休养,才能期待以后的发展。”在百度词条中的《申时行》历史评价的有这样一段话,我认为“首鼠两端”的评价是作者引用了当时与同在朝廷的官员相互对抗攻击的话,攻击申时行的粗话是对申时行不满,或者说是敌对派的言辞,是用来攻击中伤申时行的语言,不能作为历史评价申时行的依据或者观点,更不作为评论的重要依据,更不能作为评论家的代表作,他是负能量和反对声音的及个别;再者,这个言辞及其峰利,“首鼠两端”不仅对当时当朝首辅申时行大不敬,而且将皇上和所有朝廷共事的同僚官员们也是大不敬,人人比做了老鼠,因为申时行是老鼠,其他人不是吗?虽然“首鼠两端”是形容词,但对皇上和当时的同僚们也是骂了的,只不过没有人提醒此语中伤大家吧了,也没有人说这句的比喻不哈当,说实话,我不知道申时行当时是怎么反驳的,如果是我,一定说出此人的攻击对象间接就是皇上,这是慢骂朝廷命官和皇上,这也是无徳性的表现,是要受到重罚处理的,可是没有看到朝廷对这些人的处理,证明皇上的软弱与无能,被一邦所谓的朝廷命官所架空,没有实权和地位表现,申时行因立太子的事被迫辞官,实际上是皇帝与朝廷官员斗争的牺牲品。这也证明了,伴君如伴虎。在一些人看来申时行一边靠皇上,一边靠臣官们是一种求稳的心理,但也存在较性心里,多数人认为他比较滑头,我认为是一种自保的心理行为,展示了他高智商一面的智慧。尽管为了太子之位,最后辞官回家养老几十年,但他的结局是好的,在他回家几十年之后,皇上还想着他,并在最后去世时刻的封享了他,这是他一生最高荣耀,也是他最高的智商的体现结果。
三“维稳”是执政者关键
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你做什么官职,稳定才能求进步,这是普遍的心里现象与行为,大多数人在维稳中求生存,求官职,一些人就是在一辈子中维稳度过一生。维稳分二种形式,一是内维稳,一种是外维稳,通常情况外稳就内不稳定,内稳就外不稳定,这两种情况出现,应当比较好对付,但如果出现第三种情况,有可能这个官员位子就保不住了。那就是内忧外患,双向不稳,如果是朝廷,这个朝廷就要灭亡了,所有人在自己的位子上不要出现内外同忧的局面,这会使国家民族处于危险境地,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八国联军犯我中华,的确让人伤心和痛苦,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首先“要状大自己,才不受人欺负。”自己不强大永远被人欺负。申时行在首辅大臣位子上,看到了当时张居正为了权力的闹内斗真实现象,大多数时期靠皇上来支持自己的行为,当时皇上年幼,但有皇后作保证,有些东西非当时无法明白,只能听首辅张居正的。正因为皇上朝廷要听张居正的,所以,张居正才发挥自己的作用,可以将自己的梦想理、想转嫁成为皇上的理想与行动和意志力,比起申时行接任首辅大臣时,已经长大成人了,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思想及意志力,申时行是他的老师也很早看出皇上心思,也有意培养他独立处事的能力,绝不能象以往张居正那样有时候个人意见临驾于皇上,这个申时行是不做,也不会那样处事的。他支持皇上独立行事,就是树立皇上威严和威风,从而掌握更多更重要的权力;这是他求稳心理的主要表现,更是为了树立皇上的威信,长期以来,张居正与反对派进行了内斗几十年。张居正因父亲去世回家守灵,后被反对派利用空隙,反对派看到张派群龙无首,大家蜂拥而致,又导致另一场新的斗争开始。话说回来,张居正首辅为了实现自己部分理想,干了几件大事,的确让历史与后人记忆犹新,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死前也得到皇上皇后的信任和重用。所以,能干一番大事业,拿这个与申时行作比较,我认为没有可比性。第一,双方作为同朝首辅,但双方在时间上有很大差异性,张居正在前,申时行在后,这时间差异;第二,时机不同,张居正在前任首辅正是年少,对事情无判断能力,需要大臣张居正帮助,皇上年少大多数听皇后的,皇后认为张居正才智过人,对张居正信任有加,当时张居正得到了皇后信任也就得到了皇上的信任,那时皇宫正需一位他张居正那样能力水平超常的帮助扶持皇上,说白了双方都有依赖对方的需要,一个要彰显自己的能力,一个要统领天下,都想干一番事业,应当说机会和时间造就了张居正的“伟大”与“贡献”和事业的成功,说白了是皇上和太后、朝廷给了他这个最佳的机会,说得“维心”一点就是张居正他的命,但由于他首辅任期内过度彰显了自己的个性,结果死后被抄家。相反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血的教训,故而在接任皇宫首辅工作后,始终坚持“维稳”心态处各种事物,从而安稳坐了八年首辅大臣,从时间上、从作为上、从功劳和贡献看,都没有什么名气,评价他的人说他是个“和稀泥”、“和事佬”我到认为他是一个精明的首辅大臣,当然,有个别作者为了吸引眼球说申时行“无所作为的”“前怕狠后怕虎”评话,应该说这些作者对当时历史和申时行所处位子,皇上的年龄没有弄明白清楚,只知道表面张居正干了什么活,而不知道申时行为了培养皇上所做的百倍付出和努力,这是申时行最杰出的地方,也是他一生最大的功劳地方,还有一点原本是皇上的权力,因年幼已经分散给了大臣官们,在申时行看到皇上年龄大了需要独立亲政的时候,也需要将权力移交给皇上的时候,这个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路子,需要十分用心,说白了是权力的竞争,是要高智商,才能不让皇上生气,又不能得罪各位大臣,还得明正言顺将权力交给皇上,达到双赢之目的,申时行做到了。这是张居正无法比拟的地方了。这也是他与皇上和大臣们之间“维稳”最大贡献。
四、“维权”是执政的基础
在这里所说的“维权”是指申时行为了皇上的权力,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权力,帮助皇上尽快适应和主导皇上主动工作,主动作为,并真正成为皇上出谋划策的人。申时行接受首辅工作以来,应当说在逐渐放弃首辅这个角色,上皇帝尽早独立工作,快速进入领导地位,所以,在为了争取皇帝的权力上,他是尽心竭力在帮助皇上,尽量从大臣们中夺回更多权利,减少各种势力因权力而伤极同僚的做法,从而减少内斗,消耗国家成本和资源,让皇上亲政,就是归还多年来由于皇上年幼,不能独立处理问题,其实当初就是将原本皇上的权力分摊给了大臣们,由于时间比较长,这些权变成了大臣们的“福利”了,有些人不想归还给皇上的权利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便出现了“皇与大臣”明争暗斗和争权争利的现象,当然,大多数人是会那么明显与皇上斗争的,如果明争,担心日后日子不好过,既使想抗衡也会主动放弃,一些人靠这个权力获得更大利益,所以不想交权。然而,皇帝随着年龄增大和欲望肯定逐渐增加,大臣还权给皇上是早晚的事。他已经长大成人不能永远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继续放在下面,给别人使用自己确不管不问,年少不懂事,年轻少管事,中年要管事,老年要成事的心态应当得到体现和发挥,申时行是当时要面对已经成年的皇帝首辅,查阅资料,首辅解释是:“首辅是明代和清代首席大学士的习称,明朝内阁设置于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八月,其中进入内阁的官员称大学士,有别于翰林院学士。明中期后,内阁大学士又成实际宰相,称之为“辅臣”,称首席大学士为“首辅”,或称“首揆”、“元辅”。嘉靖、隆庆和万历初期,首辅、次辅界限严格,首辅职权极重,主持内阁大政,权力最大,内阁中亦争夺剧烈,次辅不敢与较。清代领班军机大臣之权极重,亦称为首辅,如清代索尼、张廷玉、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明朝的首辅是指首席内阁大学士,有宰相之权而无宰相之名。”(百度词条“首辅”注释。)笔者认为:首辅不仅是皇帝的参谋,而且是皇帝权力的组织者、执行者,发布者,实施者、监督者,从另一个侧面讲,好的方面讲,也是皇帝决策的策划者、实施者,决策者,当出现每个项目和内容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时,皇帝的首辅第一时间面对,且要告诉皇上,在张居正主政时期可以先做后报告皇上,申时期时期就不行,因为皇上年龄大了,有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也不允许申时行自作主张,即便皇上在张居正移权给了申时行,凭申时行的忠诚性格,也绝不会自作主张,一定让皇上来处理。既使申时行在当时有超越皇上的处理好方法,也会提出来上皇上参考,让皇上先说,或者皇上要他说才会说出处理的好方案,他绝对不会上由皇上难看,一定上皇上自己决策,我个人理解首辅即是皇上高参又带有老师的味道在理面,首辅出谋划策最重要,在皇上那里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有时有指导政策法规的制订与实施作用,有用人用权和掌握和判断生杀大权的权威与尊严作用;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决策一旦失失误、失当、失败,肯定就承担责任,也就会成了为皇帝的牺牲品,被皇帝用来顶包,比较典型的例子,清朝万历年间如张居正的成就与失败就是活生的例子,在生很风狂,死后确祸炴。为什么在死后抄家呢?被那个年代更加注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传统美德观念教育与传承,而且尊师重教十分盛行,传统观念十分浓厚,皇上是尊师重教的典范,所有人民都在关注他,他的一言一行影响到周围的人,同样影响他的子女,是这势必就要减少首辅及同僚的们权力,说白了,在那个年代,权力代表利益,权利代表金钱,代表银子,所以有些人把权与利看得太重,皇上也不利外的。从历史角度看,申时行对权力欲望并不强烈,只是想将首辅的部分权力归还给皇上。
总之,申时行自考入朝廷升官后,我认为性格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维姓”是性格的体现的表达,他通过复姓来证明自己人品,即“行得正座得正,坐不改姓”来表白自己的为人,此事得到了皇上恩准,恢复了申姓;二是“维圆”是高智商展示,通过圆滑从而小伤及无辜,这种方法求了不小人;三是“维稳”是执政者最重要最关键内容,作为皇上或宫廷大臣们必须要对内对外都以团结和谐为主线,只有上下团结,才能其利断金,做首辅最重要任务就是团结大多数宫廷大臣们为皇上办事和进公差;四是“维权”是执政的基础,特别是“皇权”制度下的行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上就有“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君要君王不得不亡。”现象,在万历之前可能这种皇权思想比较浓厚,到了万历皇帝这代已经明显好了许多,但维护皇权致上的申时行行为与思想是有的,我们从当时皇上处理的文件中釆取“留中”不难发现,“留中”指皇帝将臣工奏疏留置内廷,不做批答。这是李佳作者的论文发表在《古代文明》杂志第三卷第四期 2009年10月刊 [帝制中国] (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李 佳作品。有学者对一年进行统计,就有301件。有点出人意料。如:“董其昌辑《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成于天启四年(1624 年),共收奏疏 301 件(其中有 7 疏仅存目,另有 2 疏时间不明),举凡国本、食货、吏治、边防等皆有涉及。”有作者对“《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共收录奏疏 301 件,其中言官奏疏 160 件,包括六科给事中奏疏 71 件,御史奏疏 89 件。其余多为部卿、督抚之疏,内阁大学士疏仅 1 件。上述数据大致反映出,神宗“留中”言官奏疏最多。”《古代文明》杂志第三卷第四期 2009年10月刊 [帝制中国] (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李 佳作品。对这一时期的“留中”作品作了进一步说明“事实上,神宗于内阁大学士之揭帖亦多不报,其事在申时行辅政期间已为经常。申时行言:“近来事体与往时大相悬绝,阁中开导斡旋止凭揭帖,往时或奉御札,或令文书房口答,无中寝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寝者什之七八”。申时行:《赐闲堂集》卷 38《答叶台山相公》,四库全书存目本,集部第 134 册,第 791 页。这些都表明申时行编书就是为皇上树碑立卷,是在维护“皇权”上所作的努力,在当朝当时来看是有正确的一面,也是正确的选择。但从当今来看,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申时行当时不为皇上做事,也许连命都保不住。但从历史角度看过于顺从迁就皇上,使朝廷有效的运行路线没能发挥好,或让皇上个性办事的表现。
参考文献:
已在论文中各段引用中加以注明了文章来源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