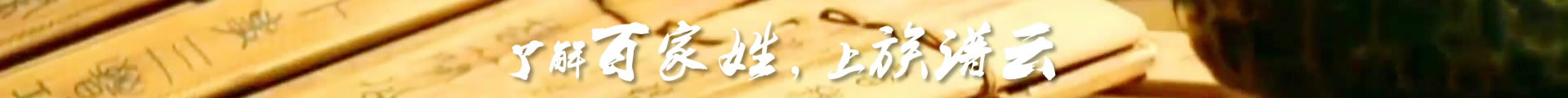回忆月光下的求学之路
今夜广州的灯火格外温柔,杯中茶烟袅袅,老同学肖光铭忽然提起:"还记得一九七八年中秋前夜,我们从学校走回去的事吗?"刘一平笑着接话:"怎么不记得,月亮亮得跟白天似的。我怔了一下,心底那扇封存已久的门,被这句不经意的话轻轻推开了。
一九七八年,恢复中考后的第一个秋天。我们这群从潭口乡考上南康中学的孩子,像一群迁徙的雏鸟,落在离家十三公里外的陌生枝头。中秋前夜,思家心切,我们几个同乡约好一起步行回家。三角五分的车票钱,对于当时的我们,是一笔需要咬牙才拿得出的巨款。
月光真的很好,水银般泻了一地。我们在学校传达室挨到深夜,心里着急,一次次探头看天色,总觉得该天亮了。终于忍不住上路,走到半路拦住一位早起修车的师傅问时间,老师傅就着路灯看看表:"刚两点哩。"大家"哎呀"一声,相视苦笑,却也没人说要回头。十三岁的我,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个子也不高,只能加紧步子跟上哥哥们的背影。那一夜的路,长得像没有尽头。砂石路面在月光下泛着白,我们的布鞋踩上去,沙沙作响。困,累,脚底渐渐发烫,但谁都不说话,只是埋头走着。走到龙岭天刚蒙蒙亮,晨雾像淡淡的牛奶淌在田野间。路过大姐家,我实在走不动了,敲门进去。大姐见到我,惊得手里的水瓢都掉了:"小弟,你怎这个时辰到了?"听我说是走回来的,她眼圈立刻红了,连声说"造孽",转身就去灶房生火。两个白水煮蛋很快端到我面前,滚烫的,她催我趁热吃:"补补元气,你还在长身体呢。"
在家只呆了两天,又该返校了。这次肩上不是书包,是三十斤大米那是交给学校食堂的伙食费。三十斤,对成年人不算什么,对十三岁的瘦小身板,却像一座小山。扁担压在肩上,火辣辣地疼。走一段,歇一阵,四五小时的路程,我们不知歇了多少回。每次放下担子,肩膀就像卸下千斤重担,可再次挑起时,疼痛变本加厉。到学校时,衣裳都能拧出水来。
那个周末回家,我鼓起勇气对父亲说:"爸,我挑不动,走路也走不动了。"父亲正在做木工活,听到这话,粗糙的手停在半空。他久久没说话,最后深深叹了口气,混浊的眼泪顺着他沟壑纵横的脸颊流下来。"知道了。"他说。下个月返校时,父亲多给了我一元钱整整一元。"坐车吧,"他声音很低,"米......我想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元钱,是他熬夜多做了很多多活换来的。
四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当年一起走夜路的少年,如今都已鬓染霜雪。我们在广州温暖的包厢里重聚,窗外是璀璨得不真实的都市霓虹。可当往事被提起,那些遥远的夜晚瞬间复活1978年的月光,依然清澈地照在今夜的笑容上。
"那时候真苦啊。"肖光铭感慨。
"可是我们走过来了。"刘一平举杯。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有些路,走过就长在了骨头里;有些重量,扛过就化进了血脉中。那夜的月光,那担米的重量,父亲的那滴泪,大姐的那碗蛋......它们从未真正过去。它们是我生命河床里最坚硬的石头,水流日夜冲刷而让纹理愈加清晰。
申祺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