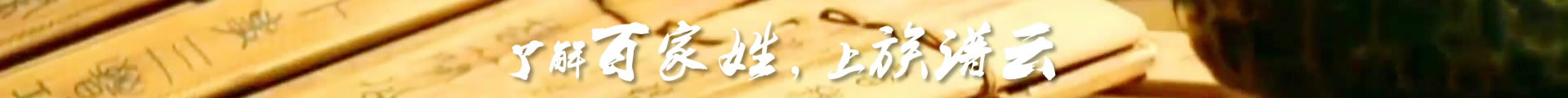我的父亲申廷义,生于一九四三年农历九月,家里九姊妹,兄弟六人,三个姐妹,父亲在姊妹中排行老二,村子里父亲的同龄人都叫他申二爷。
我族申姓起源秦朝的琅琊郡,现山东省诸诚县,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朝廷发布召书开启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移,我的入川始祖就是湖广填四川一百万人口中的一员,从湖广来到四川省的安岳县,申氏族人在安岳县的姚市镇、团结乡等地繁衍生息了六代,清同治年间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民众生活疾苦,我的高祖两兄弟又从安岳县迁徙到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州马尔康县草登乡,最后定居在金川县城厢龙王庙、咯尔乡五甲村、沙耳乡沙耳尼村。父亲是申家人入川的第十代后人,目前在金川县沙耳乡申家人的后代已延续到了第十三代。
父亲十九岁开始就跟村里的木匠师傅沈志安学习木工手艺,父亲的师兄弟有三人,父亲是大师兄,师弟是表叔魏正仁和沈老师傅的儿子沈云发,在那个年代会一门手艺活,比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种庄稼来养家糊口还是要好一些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悟性高超的手艺人。小学文化的父亲没有学过勾股定律和πr²,但学起鲁班祖师爷的榫卯结构力学来却是得心应手。在我小学和初中时候的假期里时常会看父亲工作,还会帮父亲拿东拿西的,看着父亲亲自设计并制作出来的一件件木工制品,小到桌椅板凳、床、衣柜,大到修房建屋,都凝聚着父亲的聪慧才智和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父亲的师傅是个非常严厉的人,总爱批评徒弟,父亲虽然也有被批评的时候,但父亲悟性高,师傅一点就会,也算是沈老师傅最得意的门生。小师弟沈云发刚入门数月,父亲的沈老师傅就离世了,是父亲亲手把木匠手艺传承给了他的小师弟,父亲还带了四叔申廷昌、堂哥申洪珊、堂叔申廷友、表叔朱意新学木匠手艺,他们都是父亲的徒弟,后来四叔和堂哥都各自带了徒弟,他们就是父亲的徒孙了。
父亲做过最神奇的东西是木质结构的小麦脱粒机,老家主产的粮食是小麦和玉米,小麦磨成面粉后就是我们的主食,玉米主要是用来喂猪和家禽。小麦最原始的脱粒方法是人工用梁盖来捶打,一般情况是左右两边各站一个人或多人对打,后来就有了脱粒机,劳动效率得到了提高,就是脱粒机太重了至少得有好几百斤,村子里有脱粒机的人户也不多,村民间借用和租用脱粒机的时候,搬运脱粒机就成了一件麻烦事,好几百斤重的铁疙瘩,至少得四个壮汉才能搬动,村子里的路本来就窄,还要爬坡上坎的,一点都不方便,于是父亲就用较硬的木质材料做了一台小麦脱粒机,脱粒机除了电动机、轮轴、扇叶是铁质的,其他部件都是木头的,脱粒机的重量至少减轻一半以上,工作起来效率却丝毫不减。父亲木匠手艺的收山之作是四把古式太师椅,椅子的靠背是用手工一刀一刀雕刻出来的。仙鹤与梅兰竹菊的组合图案,图景栩栩如生,这四把古式椅子是父亲最满意的作品,它也将成为我们家的传世“宝贝”。
我的父亲是一个顾全大局的领头人。平时家族里有大事小事都会来找父亲帮忙拿主意。父亲也很关心他的兄弟姊妹们,哪家有困难父亲都会主动的帮衬,在父亲的带动下整个家族都很团结。一九八一年老家农村集体合作社包产到户,开始划分土地到每家每户,老家属于大渡河流域,耕地面积少,人均分配水地(山泉水能灌溉的土地)只有四分,还不足半亩,靠种地获得的粮食只能解决温饱,其他经济收入也没有了。于是父亲开始带领他的兄弟姊妹们和一些邻居亲戚四处承包修房子的工程来做,可以增加大家的经济收入。父亲先后在金川县修建了集木乡供销社、勒龙乡供销社、二嘎里乡长线站、周山乡食站、卡拉足乡政府和兽医站。那个时候父亲几个月才能回一趟家,只有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在家里。每当一个工程完工的时间,父亲就会请上亲戚和邻居们来到家里,给他们发工资,父亲会提前买好白酒、瓜子、花生,晚上几十个人聚集在我家的堂屋和院坝里,吃着瓜子花生、喝着小酒,聊着工程中遇到的事。在这之后父亲就开始给大家算工资了,首先把成本开支一笔一笔计算好,总收入减去成本开支,剩下的钱父亲会根据每个人的出工总天数分摊成每个工时的价格,于是计算出每个人的工资收入,再数好现金一一分发到大家的手里,这个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虽然大家都增加了收入,但在外工作却也又累又危险,记得父亲讲过有一次他坐着拖拉机去拉建筑材料石灰,在回去的路途中遇上了暴雨天气,因路面颠簸导致拖拉机发生了侧翻,父亲是坐在拖斗的材料上面,直接被抛下了车,一只耳朵差一点就被挂掉了,还去医院缝补了好多针。
在没有建筑工程做的时间,父亲就去承建了县商业局和供销社商场里的货柜和货架,父亲带着他的师弟和徒弟们进行原木采购、木板加工、成品制作、漆面粉刷一条龙的施工作业,我家的院坝转眼成了父亲的加工厂,一群匠人围在木料旁忙活,有说有笑,手里的刨子 “哧啦” 作响、锤子 “咚咚” 轻敲,锯末伴着笑声四处飘散,工具的交响与打趣的闲谈缠在一起,满院都是热腾腾的烟火气。
我的父亲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商人。我们家住在省道248公路旁,公路旁有一个100多米的小坡上面,坡很陡,公路的下面就是大渡河,我家所在的那段河流因向右拐个小弯,河滩上就冲出了一条分岔的小河,村子里都叫小河边,小河边靠山和公路的地方还冒出了一股山泉水,寒冷的冬天泉水的温度在20 摄氏度左右,在洗衣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村子里的家家户户都会到小河边的泉水旁来洗衣服,特别是临近春节的时间,每家人都要搞卫生,小河边每天洗衣服的人是从早排到晚啊,我家离小河边最近,洗衣服占位子时,就会有很大的优势,因为远远地站在房背上一瞧,就知道小河边哪个时间段排队的人少,我们就飞快的用背篼背上衣服一溜烟的冲到小河边。冬天的夜里有一种叫石钢鳅的小鱼会从大河里游到小河边的泉水里来,在天亮前就又会游回大河的深水里,我们时常会在凌晨十二点或清晨五六点钟的时间,悄悄的溜到小河边的泉水旁捉小鱼,收获多的时候会捉到好几十条,小鱼烧汤和油炸非常美味,在寒冬食物匮乏的时间,能有这等美食来改善生活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父亲的交通工具是28大杠自行车,每次出门上县城回来,父亲都会抗着28大杠爬坡,人又累又不方便。父亲就在公路边自家梨树下的荒地里建了一幢小房子,房子依靠着山坡的地势错落而建,共有三层,每层的面积五十平米左右,一层用来停放自行车,二层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小厨房,三层只盖了一半的顶,有一个小房间和一个杂物间,父亲在一楼大门的正上方写上了“海峰店”。
我的家乡素有 “中国雪梨之乡”的美誉。相传,唐太宗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入藏时留下的梨籽在金川生根发芽,金川雪梨因此得名 “公主梨”。最早用中文记载金川种植雪梨的史料是清朝康熙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书中记载 “大渡河部(今金川、丹巴、泸定一带)有梨栽培”。清朝乾隆皇帝平定大小金川之乱后,金川雪梨成为皇室贡品。金川县是全世界最大规模原生态、高海拔的雪梨种植区,也是世界白梨的起源地之一。全县雪梨种植面积达 4.2 万亩,拥有果树超过 110 万株,年产量 3 万余吨。我的爷爷曾是用马帮托运雪梨到灌县换取盐巴、茶叶、布匹的养马人,随时改革开放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重庆大足、德阳广汉、德阳什邡等地的雪梨商贩带着大卡车到金川县来收购雪梨,因为商贩的车很大,只能停在省道公路的两旁收购雪梨,下乡进村的路就没法去了,同时外地人对本地也不熟悉,做起生意来很不方便,父亲瞧准了这个时机,“海峰店”就成了外地雪梨商贩们的代办点,父亲组织人手用小四轮拖拉机从各乡各村的村民手里收购雪梨,再集中到外地商贩们的大卡车上,父亲代收雪梨从来不赚取村民的差价,只按每辆车的吨位向商贩们收取六百、八百、一千二不等的辛苦费,这费用还包括商贩们的住宿和伙食费。父亲常说赚钱是小事,让家乡的雪梨能更多的销售到外地去,才是他做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因为父亲做事讲诚信,外地商贩和当地农民都信任他,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找父亲帮忙,想把自己家的雪梨销售出去,销路最好的时间,一年父亲可以代销40多车雪梨。
几年后,父亲又在公路的下方,靠近小河边泉水的方向,利用村子里分包的旱地,废弃的砖瓦厂窑洞位置扩建了第二幢两层的小楼,叫“海峰店”二单元,小楼开始的时候是父亲做木工的地方,后来就成了父亲的雪梨膏作坊。父亲的勤劳已深深地刻在了他的骨子里,古稀之年创办了雪梨膏作坊合作社,于2017年注册了海峰牌雪梨膏商标。父亲坚持传承古法熬制雪梨膏,从收购梨子、洗、榨汁、过滤,再到熬制,全过程不加一滴水,约十斤梨才熬到一斤膏。整个熬制过程约6个小时,这期间需要不间断地添加柴火,每个过程要细心和体力、耐力。每到秋冬时节,梨子丰收的季节也是父亲最忙的季节。在古法熬制雪梨膏的环节,父亲十分讲究器、水、火,器皿不能是铁器,锅、盆等都必须是搪瓷的,水分蒸发过程过滤多余的果纤维,火候靠不间断地添加柴火来拿捏等等。因为熬制雪梨膏需要辛勤劳作,父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他对古法熬制雪梨膏的工艺要求始终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父亲的作坊放开祖传雪梨膏的秘方,在整个熬制过程中,当地村民都可以参观学习。父亲认为“手艺熟练,虽然地位不高仍然坚持”就是一种工匠精神。自己坚守古法熬制,就是要树立标杆带好头,希望当地人把盛产的雪梨好好利用起来,熬制正宗雪梨膏,把这一行传下去,把金川雪梨、雪梨膏远扬出去。目前父亲已成功申请了古法熬制雪梨膏的非遗传承人,同时把手艺也传承给了二姐和侄儿们。
如今的小河边公路两旁从“海峰店”一单元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12户人家,有二姐家的农家乐、开酒厂的、开民宿的、做仓储的等等。二姐家的“鑫河梨花村农家乐”是在父亲的“海峰店”二单元旁边流转土地上而建的,父亲的雪梨膏产品就放在二姐家的农家乐里由二姐帮忙销售,每年还是有两三万块钱的收入,父亲现在的交通工具也从28大杠换成了电动三轮摩托车。
我的父亲是一个重视教育和家族文化的传承人。家族资料记载,我家祖上就没有文化人和吃朝廷俸禄的人,父亲他们那一代人的童年正处于新中国伊始,农村经济条件差,没有机会学习文化。我的高祖与嘉绒藏区“五大土司”生意往来在金川攒下了丰厚的家业,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家,但被恶霸家掠夺了财产,并害死了我的高祖。就因恶霸家的人是朝廷的一个带兵管事,民国初期还任职于官府。同时在土改运动时期受奸人所害,给家族扣上了莫须有的阶级成份。在血淋淋的教训下,父亲对下一代的要求就是要读书学文化,出人头地,自己要强大,家族要团结,才不被外人欺凌。在我小时候就常听父亲念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父亲坚信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家族中如果有哪个兄弟姊妹要是不想读书了,肯定会被父亲痛批一顿,渐渐地父亲在家族中树立起了很高威望。
父亲给我们姐弟四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家里再困难,只要我们想读书,花费在学习上的开支父亲从来不会吝啬。在父亲的支持下大姐是全日制本科生,从事行政工作;二姐中专,县里的民营企业家,从事餐饮企业管理;三姐中专卫校,在职本科,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我是全日制专科,在职硕士研究生,在央企通信行业工作。虽然我们姊妹四人也许还没有达到父亲的要求,但是我一定要传承好父亲的教导,培养好我的孩子们,我相信在我们一代两代三代人的努力下,我们的家族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文化传承,我们家是有一部分老家谱资料的,但在文革时期全部被抄家损毁了。1994年父亲牵头在我们家里启动了制谱工作,1995年乙亥春编撰完成第一版《申氏家谱》,共发廷字辈23本,并在“才啟三天雲,国仕在朝廷;洪正新万顺,大清明自安。”二十个字辈的基础上又增加十个字辈“良杰显忠孝,玺玉九乾坤”,并书信于安岳老家的族人,建议由安岳老家再议十个字辈。
2005年乙酉春首次修谱,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在第一版家谱的基础上进行了人员信息的完善,父亲组织了家族大会,并商议定期举行家族大会,对家谱进行修补。2024年春节正月初二在父亲的安排下,我们组织召开了家族会议,由我和另外三个洪字辈的兄弟、一个正字辈的侄儿负责启动了二次修谱工作,我们计划在2025年内完成第二次修谱,修谱完成后全部录入申氏人的网站族谱云。
这就是我的父亲申廷义,申氏入川第十代后人,乡邻敬称“申二爷”。他十九岁学木工,悟性高超,以小学文化精通榫卯技艺,不仅传承手艺给师弟与多位族人,更巧妙制作木质小麦脱粒机,以木雕太师椅为收山佳作。作为家族的领头人,他带领族人和乡邻承包工程增收,险遭车祸,仍然坚持着。建“海峰店”品牌为家乡雪梨代销,古稀之年创办作坊,成为古法熬制雪梨膏的非遗传承人。他重视教育,培养出四个优秀子女,更是两度牵头修撰《申氏家谱》,增续字辈,以匠心与担当凝聚家族,传承文脉。回顾父亲八十三载春秋,拳拳赤心,山高水长。家族之幸,后辈之幸!
乙巳年冬 申基

我的父亲(穿着羊皮夹子)

父亲的海峰店

父亲的雪梨膏